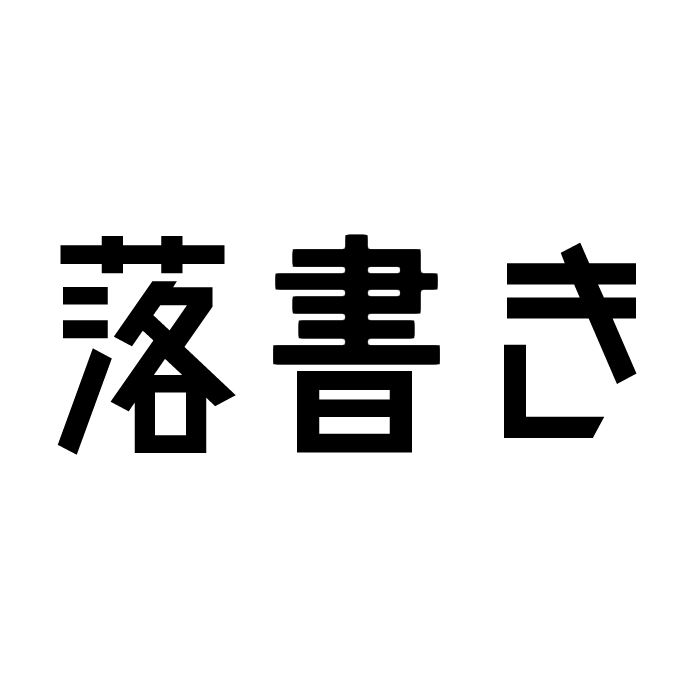欢迎回来,我们今天将会讨论一个有趣又略显沉重的话题——死亡。我们从一位伟大的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内心挣扎开始。他功成名就,却在死亡面前感到一切虚无,这引出了一个根本问题:面对死亡的必然性,我们的人生究竟有何意义?这难道不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叩问吗?
《伊凡·伊里奇之死》
托尔斯泰将他的困惑写进了小说《伊凡·伊里奇之死》。伊凡的一生看似成功,却在病痛中逐渐意识到自己的渺小和死亡的逼近。他先是逃避,然后是痛苦,最后才似乎找到了某种平静。这好似暗示了,面对死亡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深刻的自我认识和转变,而这部小说,就像是对托尔斯泰自身问题的一种文学化表达和探索。
哲学长河中的回响
托尔斯泰并非第一个提出这类问题的人,从古希腊到启蒙运动,再到20世纪,哲学家们似乎一直在试图回答这个问题。有趣的是,托尔斯泰自己也尝试过哲学,但并未找到安慰。这是否意味着,哲学本身并不能提供简单的答案,反而可能揭示问题的复杂性?我们不妨看看,这些思想家们是如何一步步探索这个深渊的。
古希腊
柏拉图
“either it is annihilation, and the dead have no consciousness of anything, or, as we are told, it is really a change–a migration of the soul from this place to another.”
Plato, Apology, in The Collected Dialogues of Plato
让我们回到源头,看看古希腊的智者们是如何看待死亡的。柏拉图告诉我们,死亡要么是彻底的终结,要么是灵魂的迁徙。他似乎并未急于下结论,而是将选择留给了我们。这似乎意味着,关于死亡的本质,本身就存在着不确定性。而我们作为活着的人,又该如何在这种不确定性中找到自己的立场呢?
哲学作为死亡的准备
Those who really apply themselves in the right way to philosophy are directly and of their own accord preparing themselves for dying and death.
Plato, Phaedo, in The Collected Dialogues of Plato
在《斐多篇》中,苏格拉底面对死亡时,竟显得异常平静。他甚至说,真正的哲学家其实是在为死亡做准备。这听起来有些奇怪,难道哲学的目的不是追求知识,而是学习如何面对死亡?苏格拉底似乎认为,哲学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不断追求智慧、超越肉体局限的努力。那么,这种对死亡的准备,是否就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
伊壁鸠鲁学派
So death, the most frightening of bad things, is nothing to us; since when we exist, death is not present, and when death is present, then we do not exist.
Epicurus, “Letter to Menoeceus,” in The Epicurus Reader
死亡并非坏事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相信灵魂不朽。对于那些认为死亡是彻底毁灭的人来说,恐惧便油然而生。伊壁鸠鲁提出了一个非常直接的论证:既然死亡意味着感觉的丧失,那么它对我们活着的人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当我活着时,死亡尚未发生;当我死亡时,我已经不存在了。这似乎意味着,我们不应该害怕死亡,因为死亡本身对我们来说是无关紧要的。
物质主义与生活
伊壁鸠鲁的论证建立在一个物质主义的世界观上——他认为万物都是由原子构成的,包括我们的灵魂。那么,如果构成我们的原子集合解散了,我们也就随之消散了。这好像在说明,死亡就是一切的终结。如果是这样,那么哲学的作用,就不仅仅是理论探讨,更是要帮助我们消除这种恐惧,从而更好地享受当下的生活。这与苏格拉底的观点相比,似乎更加务实,但也可能少了些超越性的维度。
早期基督教
“If the dead are not raised, then Christ is not risen: and if Christ be not risen, then our preaching is in vain, and your faith is also in vain […]. Let us eat and drink, for tomorrow we die.”
Cor. 15:13-14, 15:32. KJV.
圣保罗的复活论
随着基督教的兴起,死亡的讨论发生了变化。圣保罗强调,复活的信念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他甚至说,如果没有复活,那么信仰就是空谈。这是否意味着,对于基督徒来说,死亡并非终点,而是通往另一种存在的桥梁?如果没有复活的希望,生活是否就失去了意义,只剩下及时行乐的念头?这与伊壁鸠鲁的观点形成了鲜明对比。
When the perishable has been clothed with the imperishable, and the mortal with immortality, then the saying written will come true: “Death will be swallowed up in victory.” “Where, O death, is thy victory? Where, O death, is thy sting?”
1 Cor. 15: 54-55. KJV.
保罗进一步引用经文,说死亡终将被胜利吞灭。这是否意味着,通过信仰,人们可以战胜死亡的最终性?这种对复活的信念,是否为生命提供了新的意义框架,一种超越个体生死的宏大叙事?这与之前哲学家们更多关注个体如何面对死亡,似乎有所不同。
中世纪
奥古斯丁的反思——双重死亡
奥古斯丁的经历则又是不同,朋友的突然离世,让他开始审视自己。他感到困惑,甚至痛苦,称死亡为最残酷的敌人。这是否说明,即使有了复活的希望,死亡的阴影依然笼罩着生者的心灵?奥古斯丁似乎意识到,活着的人,是在经历死亡的过程,而不是死亡本身。这是否触及了死亡体验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对生者的深刻影响?
奥古斯丁进一步提出了双重死亡的概念。除了肉体的死亡,还有一种灵魂的死亡,即与上帝分离。这是否意味着,即使肉体复活,灵魂也可能面临另一种形式的毁灭?这种对地狱的恐惧,是否为之前的复活论增添了一个新的维度,使得死亡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和令人不安?
文艺复兴
蒙田的行动召唤
“To practice death is to practice freedom. A man who has learned to die has unlearned how to be a slave.”
Michel de Montaigne, “To Philosophize is to Learn How to Die,” in The Essays: A Selection.
到了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对中世纪那种天堂地狱的二元对立似乎感到厌倦。 蒙由重新拾起宁苏格拉底那句哲学就是学习如何死亡。这是否意味着,人们并始回归对今生今世的关注,思考死亡对当下生活的意义?蒙田的哲学,似乎更侧重于个人如何在这种有限的生命中找到安宁。蒙田似乎认为,死亡不是让我们绝望,而是召唤我们行动。他说,懂得死亡的人,也就懂得了如何摆脱奴役。这是否意味着,直面死亡的恐惧,反而能让我们获得真正的自由?与其担忧来世的奖惩,不如专注于当下,勇敢地生活。这是否提供了一种不同于宗教或纯粹哲学思辨的、更贴近生活的态度?
斯宾诺莎的最少思虑
“A free man thinks of death least of all things, and his wisdom is a meditation, not on death, but on life.”
Benedict Spinoza, The Ethics
然而,斯宾诺莎似乎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自由的人几乎从不想到死亡。这与蒙田的观点截然相反。难道忘记死亡,或者至少不被死亡所困扰,才是更高明的做法吗?斯宾诺莎似乎认为,真正的智慧在于沉思生命本身,而不是死亡。这意味着,克服死亡恐惧的最佳方式,是全身心地投入到生活中,而不是时刻提醒自己死亡的临近。
20世纪
海德格尔与列维纳斯
进入二十世纪,死亡再次成为哲学的核心议题。海德格尔和列维纳斯这两位思想家,都赋予了死亡极其重要的地位。海德格尔认为,理解死亡是理解我们自身存在的关键。而列维纳斯则认为,死亡是伦理责任的起点。有趣的是,列维纳斯曾是海德格尔的学生,但他们的思想却走向了截然不同的方向。这似乎暗示着,对死亡的理解,可以导向两种根本不同的哲学路径。
海德格尔的向死而生
海德格尔提出了向死而生的概念。这听起来很深刻,不是吗?它似乎是在说,只有当我们真正意识到自己会死,并且以此为基础来生活时,我们才能活得本真。这好像在说,逃避死亡,就是逃避我们自己。然而,正如我们之前看到的,伊凡·伊里奇最终找到了平静,这似乎超出了海德格尔理论的解释范围。这暗示着,仅仅向死而生可能还不够?
列维纳斯的他者的呼唤
列维纳斯则提出了另一种可能性。他认为,死亡最重要的启示,不是关于我们自己,而是关于他人。我们对他人的责任,是先于我们自身的存在而存在的。这似乎意味着,真正的伦理关怀,源于对他人脆弱性的认识,以及由此产生的责任感。如果死亡提醒我们生命的有限,那么它是否也提醒我们,要珍惜与他人的联结,并承担起相应的责任?这是否能为我们最初的问题——生命的意义,提供一个更完整的答案?
回顾
经过这番探寻我们似乎看到了两种不同的路径:海德格尔引导我们向内,通过直面死亡来实现自我。而列维纳斯则引导我们向外,通过关怀他者来构建意义。那么,哪种理解更为完整呢?或许,真正的智慧在于认识到,这两者并非相互排斥,而是相互补充。可能列维纳斯的观点更能回应托尔斯泰的疑问:生命的意义,不在于对抗死亡的终结,而在于我们与他人的关系中所展现的爱与责任。
我们的旅程暂时告一段落。但我们内心的叩问,是否也随之结束?或许,真正的智慧并非在于找到一个最终的答案,而在于持续地追问,不断地反思。
那么,诸位,你们认为呢?
参见
[1]. Justin R.Murray. Death, Being, and Other: Heidegger, Levinas, and Tolstoy on Death
[2]. Lev Nikolayevich Tolstoy. THE DEATH OF IVAN ILYCH
[3]. SHELDON HANLON, B.A., M.A.. LEVINAS, SINGULARITY, AND THE RESTLESS SUBJECT
[4]. Mathilde Norg. Death as Guide to Life: Levinas' critique on Heidegger's notion of Being-toward-death examined
[5]. 福若眞人. 他なるものへと応答する〈倫理〉的主体性の諸相—レヴィナス思想における「死」と「教え」の教育人間学的意義